流行音樂日新月異,香港樂壇永遠不變的就只有其不斷演變的特質。與此對照的,就是百年老校不變的文化特質和傳承。今期《分號》主題專訪,我們邀請了三位出自同一所中學的音樂人,包括資深填詞人 都會大學周耀輝教授、資深電台DJ 黃志淙博士 以及 新一代編曲人 Perry Lau 一同返回他們的母校 —— 英華書院,與幾位來自英華書院Band Society的在學中學生進行一場跨越世代的深度對談。
|問:中學時期的教育有沒有影響你們成為一位音樂人 / 文化人?學校是如何影響你們的職業生涯?

黃志淙:「當時有很多的自由空間…..小時候自己有去看過經典電影Saturday Night Fever(1977) 和 Grease(1978)。那時候學校在九龍塘,同學們放學後有試過『拉大隊』去睇戲,有一起睇過Alien(1979)。我們會聚在一起討論流行文化。因為當時娛樂選擇不多,沒有手機,沒有電腦,沒有Tik Tok(抖音),甚麼都沒有,就比較容易有這種氛圍。
當時我有一位好朋友家境比較富裕,有能力買黑膠碟。他會將歌曲錄進cassette帶(卡式錄音帶)給我聽,有David Bowie、坂本龍一這些巨匠的音樂。當時電台不是經常可以聽,也不會有手機,所以這對我影響很大。迷上了這些音樂之後,我就進入了電台,而這條軌跡就繼續行走了 40 年,繼續推介這些巨匠的音樂。之後還有機會可以親身遇見他們,與他們成為朋友。
所以那位好朋友對我的影響是一輩子的,他的名字叫林偉強。記得1982年的時候,我和他一起被邀請在聖誕派對回到學校禮堂做DJ用黑膠打碟……這段經歷也是影響我一輩子的。一個大循環過去,幾十年過後,現在我也會經常在DJ Party用黑膠打碟……生命真是有趣。」
周耀輝:「中學階段與我後來的音樂事業之間的關係很難說得清。我沒有怎麼在中學階段接受過音樂教育,我甚至連學樂器都沒有。當時有師兄在學校教過結他,我『傻更更』走去學,學了三堂之後他便說我的手指太肥、太粗、太短,後來我才發現這根本是假的(笑)……
我中學畢業的時候不懂樂器,不懂樂理,也不懂很多歌曲。只是不知為何後來我會成為了一名填詞人,一填便是3、40年。因此我得到了一個結論:不一定要懂得樂器,不一定要有音樂底子才可以發展音樂路。這不應該成為阻攔你的障礙。」
Perry Lau:「我由小學開始已經是Choir(合唱團)的伴奏,直到中學畢業。伴奏和編曲其實很相似,都是要去serve(服務)一個主體,不可以有太大的ego(自我)。我要去帶領其他樂手,收起自己,同時去融入其他人。
我所有的音樂養分都可以說是從中學時期吸收。除了合唱團以外,當時的音樂老師李寶龍老師(李sir)會把我扔進不同的音樂團體,有玩過敲擊,有玩過單簧管,又被安排在學校早會以管風琴伴奏……就算今日我為流行音樂編曲,有某些元素例如Jazz(爵士樂)、Classical(古典音樂),甚至乎一些中國藝術歌曲,我都是在當時吸收。而我會開始編曲,都是因為受李sir所影響。
所以我所有音樂的養份和root(根基),都是中學給予我的。」
|問:你們會怎樣形容2025年的香港樂壇?

魏兆澧 同學(中六生):「我對廣東歌的刻板印象是小時候爸爸車上播的CD,他播的歌曲很懷舊,例如會有張國榮。後來我擁有自己的電話,再上網聽現在的廣東歌,就覺得和舊時年代的歌曲風格差異很大……我覺得這是一種進步,代表樂壇不會只留在comfort zone(舒適圈),創作者會願意突破自己。」
陸彥希 同學(中六生):「我覺得是一種變化……我認為香港一直都是向整個世界邁進,會有不同的文化衝擊我們,邁入香港的面目。例如我前幾日在聽Gareth T(湯令山)的album(專輯),真的和以前的廣東歌完全不一樣。我覺得(香港樂壇)就是一種變化,永遠都會有不同的感覺。」
黃志淙:「你們的答案都和我的學生很相似……(你們接觸的音樂)碎片化得來,又會跨時代地有少許接軌。
早前叫兩班加起來六十幾位同學每人分享一位歌手,陳奕迅只是出現了兩次……以前應該差不多半班都會說他。現在有人會介紹日本的visual rock(視覺系搖滾),有人會介紹metal band(金屬樂隊),有人會介紹台灣的樂隊 甜約翰,反而沒有人介紹Blankpink。
這幾年就數量而言,其實廣東話派台歌多到應接不暇,有很多歌曲你根本接收不到就已經消失了,有很多新人拿完獎第二年就已經(與觀眾)講拜拜。對於創作者而言,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時代。以前大家可能會慢慢醞釀或者慢慢愛上一些歌曲,如今卻很難。這種情況也不只侷限於香港,而好處和壞處都會有。」
周耀輝:「現在的香港樂壇百花齊放……我會覺得是一件好事。樂壇的『多元』比起判斷『誰做得更好』更加重要。如果你只觀望作品的話,整個樂壇都生態是是很開心的。
但如果觀望(在樂壇)工作的人,我就會有點擔心。創作人可以如何生存呢?我們的樂壇發展了這麼久,好像要『搵食』也不是這麼容易……譬如我眼前這四位年輕人,我四位師弟,我應不應該鼓勵你們入行呢?其實音樂作為一種行業好應該鼓勵年輕人參與更多。但去到2025年,大家依然好難入行…..入行之後又該如何維持自己的生計?如何得到合理的報酬?如何承受精神健康的挑戰?這些又是其他大的難題。」
Perry Lau:「我覺得正如剛才耀輝所言,在當今樂壇工作其實很艱難,非常competitive(具競爭性)。
聽到很多很『速食』的歌……不是說不好,一方面這些歌曲回應了世界的許多變化,但感覺比起以前更難見到一些賣concept(概念)的專輯,整個行業的生態也不同了。現在會見到藝人有轟炸式的宣傳,而且歌曲的題材有些太生活化。如果將歌曲比喻成寫書本的話,以前的作品是一本書,現在的作品就是一個廣告。
另一方面,我覺得現在香港樂壇很多流行的聲音都越來越壓抑。有很多用作療傷的歌曲,很多好 “Emo” (情緒化 / 憂鬱)的歌曲,又或者是一些很『硬淨』的Hip Hop(饒舌)……我覺得是香港人的情緒很壓抑。」
|問:你們認為音樂除了純粹的娛樂之外,還有額外的文化使命嗎?

周耀輝:「我自己從來都有使命感。當我回想年輕時為何要寫歌詞,我沒有想過要名利雙收,也沒有想過會成為一份職業。我會想寫歌詞,是因為我有東西想講……..」
(此部分內容僅供特定級別 Patreon 訂閱者專享,立即訂閱支持我們營運獨立文化媒體:https://www.patreon.com/interludehk)
|問:你們認為10 年後的香港樂壇會是甚麼模樣?

魏兆澧 同學:「我覺得樂壇會比起現在更加複雜,更加難。我認為以前的音樂比較純粹……現在的音樂比較多包裝,有很多考慮,很多訊息不能直接講出來……所以十年後的樂壇會更加複雜更加難。」
莊恩樂 同學(中六生):「我覺得樂壇會變得更加多元,不同風格的音樂會混合在一起,同時會更混亂,因為甚麼風格都有一點。」
陸彥希 同學:「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10 年後的香港樂壇可以展現香港的獨特性。就好像講起南韓的音樂,就會聯想起『男團』『女團』。那時候會不會可以有一個形容詞表達到本土的音樂特色呢?」
黎昊熙 同學(中六生):「可能 10 年後香港的經濟水平高一點,大家更有資源,會更傾向培養不同的興趣。可能會有更多人學樂器……我覺得 10 年後的香港樂壇會有更多人創作自己的音樂,而不是只有幾位音樂家。」
周耀輝:「不知道怎麼去思考 10 年後……回想 10 年前,20年前,也沒有想過現在的情況。所以我不會去思考實際上 10 年後會是怎樣,不如好像Steven(黎昊熙 同學)所言,我們去幻想。希望10 年後的樂壇一片蓬勃,大家喜歡玩音樂就玩音樂,又可以透過音樂生存得到,音樂類型百花齊放,香港可以成為一個音樂之都……那就好了。」
黃志淙:「啟德體育館開了之後,都有很多新的局面。Coldplay開了個頭,之後又有一些本地的藝人一齊玩。其實新的場地就是一個載體,可以有很多可能性。Live music(現場表演)對音樂很重要,譬如我們小時候總愛去日本睇表演,因為當時香港沒有份,但慢慢地香港都有一席位,還有一些大型的音樂節如Clockenflap。
而科技亦會是另一個很大的議題。科技會不會取代(人類的音樂)我不知道,但都會有一種模糊性 —— 專業音樂人與業餘音樂人之間的差距會被縮小。英國有一位備受尊重的學者和音樂人Simon Frith也有說過這個論點……其實現在很多『派台』的歌手,都是以業餘的身份去做一個專業的音樂人,但以收入而言又未能符合專業的門檻……其實這也可以是一件好事,雖然未必能賺到錢,但我們可以繼續透過音樂進行社群的建立。可能你本身是一名醫生、一名律師、一名老師,但都可以透過音樂找尋喜悅,分享快樂。這不單是香港的情況,而是全世界共同發生的現象。」
無論樂壇怎變,香港怎變,世界怎變,我相信不變的始終會是音樂人對創作的熱誠。願你們能繼續篤信自己心中的善行,再投射至自己的作品,將薪火代代相傳,一同照亮廣東歌的明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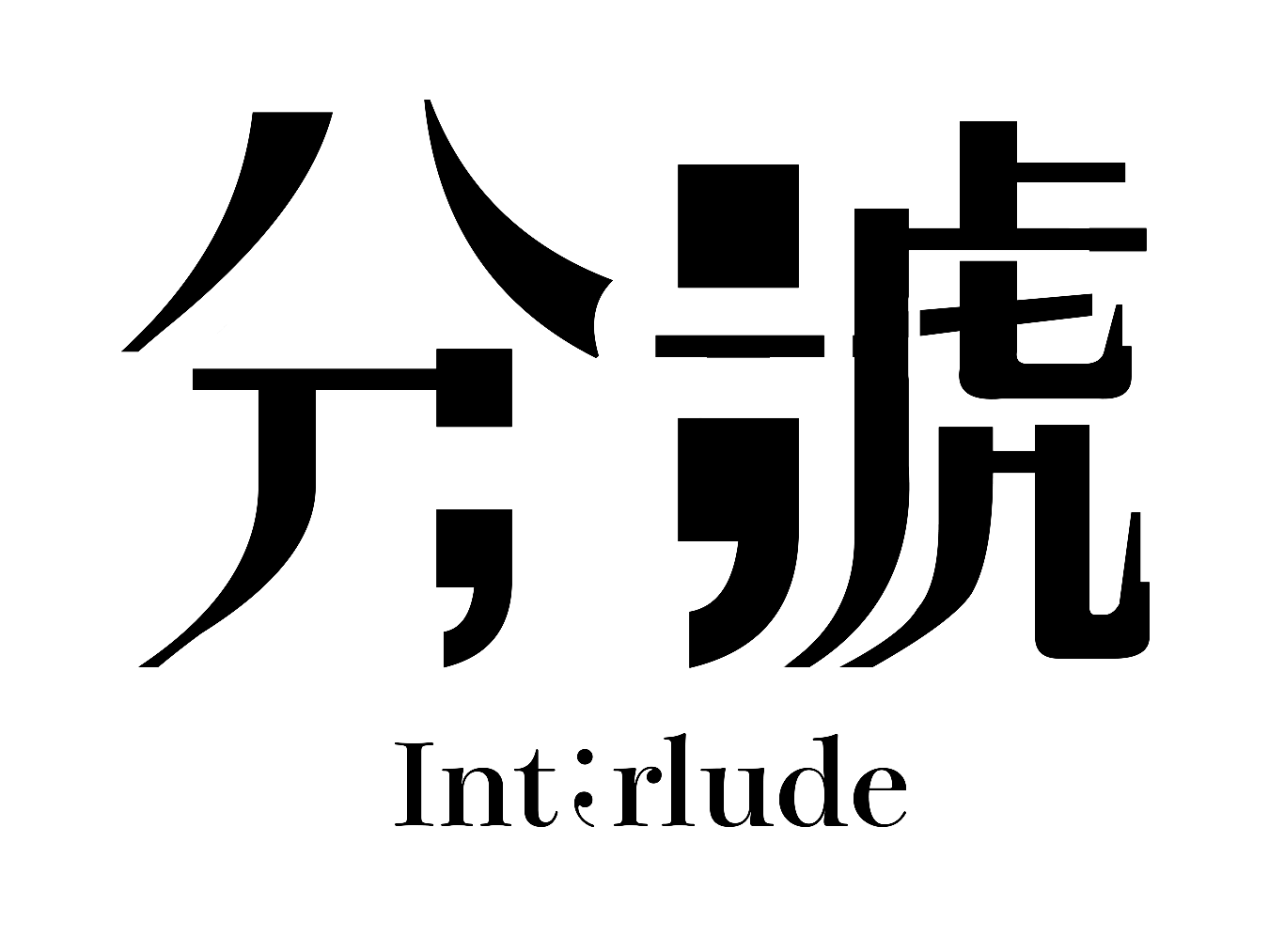


發佈留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