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言
據說在五萬年內,尼加拉瓜瀑布將會完全磨走山脈。最堅硬的石頭被最柔軟的水所溶解,這是我們相信的故事。「天下之至柔,馳騁天下之至堅」。但願維持著你意志的,不是倔硬的仇恨,而是柔軟的希望。
「如果可以選擇,我選擇寧靜。」鍾雪(素恩)向著夜空默默打起手語。「用雙手,自由自在,表達。」

無聲勝有聲,在寧靜中聽見自由 —— 應該是黃修平在《看我今天怎麼說》最想達到的效果。創作必須善良,一份作品有沒有打從心底展現同理,一般都是感受得到。而在黃修平的世界,身份認同沒有對錯,聽力程度不代表地位高低。小野(盧鎮業)的評語說得很好 —— 心臟柔軟而強大,完成度高。《分號》日前有幸採訪在英國宣傳《看我今天怎麼說》的黃修平,嘗試了解這種柔軟和強大是從哪裡來到哪裡去。

「我唔想有更多手語,都唔想有更多人工耳蝸,我想有更多自由嘅選擇。」黃修平托一托眼鏡,望向遠方。「可能健聽人嘅觀念真係唔容易放低,好多人問我係咪唔相信聽障科技,點解手語口語唔可以並用。」黃修平不禁苦笑「點解我地唔可以少啲理論,多啲理解?」
三個青年,帶著不同程度的聽障尋找自我,故事簡單而實在。「我唔想用一個聽人嘅身份,攞住幾個老掉牙嘅道理就用兩個鐘說教。屬於聾人嘅故事唔應該係咁 」 電影刻畫出不同群體的角力,卻沒有誰比誰高尚。在另一個宇宙,健全的子信(游學修 飾)可以聽到海的聲音,素恩(鐘雪瑩 飾)可以不再勉強自己融入主流社會,Alan(吳祉昊 飾)可以擺脫聽障的促博。其實何止聽障人士?所有人都背負某些障礙 —— 性格上的缺憾,某些過往的創傷,難以解釋的恐懼。生活本來就很困難,而我們都值得被體諒。我估計黃修平希望帶出的討論不應停留於聽障群體。所有人都有資格被愛,如果《看我今天怎麼說》令我們變得更柔軟,柔軟得更強大,就是一套好的電影。

「哈哈,我好似六套戲都係講呢啲。」的確,這種尋找自我,堅持自我的信念,一直是黃修平的電影語言。筆者依然記得12年前的《狂舞派》,阿花(顏卓靈)在輪椅撐起身,拖著傷腳跳舞。但電影世界很大,為何黃修平眾裏挑一總要拍「夢想」?一切卻要追溯到他的啟蒙電影《暴雨驕陽》(Dead Poet Society)。其中有一段對話是這樣的:
McAllister: Show me the heart unfettered by foolish dreams and I’ll show you a happy man. (唯有不被無謂夢想左右的人才是快樂的)
John Keating: But only in their dreams can men be truly free. ‘Twas always thus, and always thus will be. (唯有在夢中的人才是自由的。以來如此,往後如是。)
McAllister: Tennyson?
John Keating: No, Keating.
「呢一幕我記得呀…… 係呀佢問佢邊個寫」黃修平邊看邊碎碎念,微笑道:「好深刻,我有幾個朋友當年喺戲院睇完,即刻衝去尖東海傍大叫。」黃修平語頓:「佢係一套屬於解放年代嘅作品。」
解放年代……黃修平指的解放年代是甚麼?是今天還是過去?是奔放還是壓抑?生於1975年,黃修平經歷過香港的盛世和低潮 —— 80年代新浪潮;90年代喜劇武俠,百花齊放的港產盛世;回歸後資金撤走,政治動盪導致創作受制肘,黃修平都看在眼內。2008年許鞍華的《天水圍的日與夜》(The Way We Are),成了黃修平作品 《狂舞派》(The Way We Dance) 《看我今天怎麼說》(The Way We Talk)的靈感,可見港產片對他的影響。可能在他眼中,任何時代的香港都正在解放。
|從哪裡來?
「太自由喇,自由得濟添呀。」一說起過去,黃修平便喜形於色。「好多人覺得香港最盛世係80年代,但我嘅啟蒙反而係十年後。」90年代確算是香港的最風光,一方面文化產業漸趨成熟,另一方面97步近,大家都想將要說的話盡快說掉。而對初中的黃修平來說,太多東西都太震撼。校內的舞台劇,校外的電影,音樂,文化,一切都很「新」。「我好記得果年聖誕阿飛正傳上畫,有個同學睇完返到學校話套戲好悶。但佢越形容套戲點悶,我就越覺得有趣,影住張國榮背影成分鐘喎,淨係想像都覺得好睇」急不及待觀影後,他至今仍回味三分:「好震撼啊。果種色調,濕懦,紀錄片般嘅現場錄音,都係以前無見過…… 我仲好記得我睇嘅版本,梁朝偉係出現兩次,係首尾呼應黎。」 同類分享還有歲月的童話,世紀末暑假,大時代,只見他雙眼都發了光。

黃修平就是在這樣的作品之中成長,而這種任性,創新的風格都由社會延伸到學校。中五早堂遲到,施施然拿著潮州粉果進班房吃,卻在課餘千辛萬苦搜羅攝影器材鑽研拍攝,到電影中心欣賞難懂的藝術電影,校園的自由令他的電影夢得以成真。「我Prefect黎架,哈哈哈……. 當然當時一切都係文藝嘅泡沫,其實我地無明白到作品嘅內涵。例如當年大人煩惱緊97,細路仔當然唔理解。」那時他中四,在朋友家的14寸電視看了悲情城市「……咁係覺得好有feel,啲鏡頭好定畫面好生活化。但我係十幾年後先知咩係二二八事件。」天真而創新,避過了很多絆腳石。
但97的確發生了,而電影始終是一盤生意。千禧後港產不再賣錢,豪華海運結業,千座影院消失,早兩天嘉禾也走了。黃修平繪形繪色形容的香港電影好像離我很遙遠。上月《藝文青》總編紅眼寫了一篇文章,說香港是失去了海運,也失去了地運。香港正在面對一個煙霧彌漫的未來,柔軟的心臟要到哪裡去?
|到哪裡去?
「條路係越來越窄,但又越來越多人行,咁咪要搵方法。」值得討論的是,其實黃修平把《狂舞派》續集獻給了試當真。《狂舞派2》是一條時長8分鐘,免費串流於Youtube的劇情網片。網絡短片是未來嗎?「其實長片都有好同唔好。都有水過鴨背賣弄技法。。。嗯。。。太輕易嘅媒體當然會製造廉價嘅作品。但以前電視剛出現啲人都話我地會因此變蠢,結果都唔係咁。我覺得唔應該有咁保守嘅心態。」任何時代都是當代,在一切不斷創新的年代,黃修平選擇拒絕說不。吊詭的是試當真本來就是一班電影從業員,在疫情困境下另起爐灶的成品,他們其中一條短片,有一段對話是這樣的:
律師:你可以有一百個理由唔睇港產片, 但如果你真係愛香港電影的話, 一個理由就夠
審查官:……
律師:你真係要為左一百棵枯萎嘅樹,放棄一整個森林呀?
審查官:如果佢有一百棵枯萎嘅樹,咁佢仲係咪 ……
律師:睇下個森林有幾大囉。不過如果你再唔睇嘅話,就只會越來越細。
這當然牽涉香港電影值得「盲目支持」與否,或者質素足夠與否的各種討論。但至少,電影業堅持香港exclusive而不斷創新,是觀眾有目共睹的。「大家都要拍得更好」黃修平又托一托眼鏡「上年年底我去慶功,有一對夫婦走過黎,佢地話好鍾意呢個年代嘅港產片。以前嘅戲淨係打打殺殺,而家嘅戲好多元,令佢地睇個世界唔同左。」世界複雜了,但我們的經歷豐富了。近年的首部劇情片計畫,劇本孵化計劃令許多年輕的故事被拍成電影,單單今年的《虎毒不》,《不赦之罪》,《寄了一整個春天》甚至是《看我今天怎麼說》都是很好的例子。有人說這是《鏗鏘集》式電影,又有說回歸後的港產片不再專精一范。其實沒有方向,才有更多方向。
「我覺得而家新生代,中新代導演嘅題材都好創新。陳健朗嘅《手捲煙》我竟然睇到吳宇森嘅風格。」壞時代當然是好作品的溫床,但創新不必然代表好,「好橋」只能是「好作品」的最初一步。黃修平又強調:「題材係喺倒。但我地都要拍得更有要求。」
|不斷進步
和初試編導,25年前正在製作《燦若繁星》的黃修平相比,現在的他似乎對自己更嚴苛。「我以前喺一種太離地嘅文藝氛圍下成長,做文青就係會有種囂幸嘅心態。『拍左先啦!』『可能剪剪下得呢』,當你對藝術同求真嘅追求有更紮實嘅體會,你就只能夠徘徊喺始終都追唔倒嘅狀態,係幾痛苦」他將創作比喻畫畫:「當你有更高嘅技巧,你唔可能用返童年嘅心態畫啲好天真嘅畫,當然兒童畫往往係最好睇,但格硬用返同一種畫法,只會變成最虛偽嘅作品。」
創作要一直向前走,做人亦如是。對話忽然又回到Dead Poet Society「我當然係一個自由主義嘅人。 但我已經唔係15歲。今日再睇呢套戲我見倒呢套電影係Male gaze嘅,傳統同自由係絕對對立嘅,呢啲都唔係我今日可以義無反顧地認同。佢依然係屬於解放年代嘅作品,但我地唔可以停留喺齋講解放。」《天堂春夢》是這樣說的:電影是時代的見證者,能反映卻不能改變,一如周星馳的至尊寶執意介入歷史又悟其無法逆轉。Dead Poet Society只能永遠留在1989年,但我們不能。黃修平選擇不斷進步,寧願感受自己始終「追不到」的痛苦。

而一個人不斷進步是不足夠的,我們正在凝視一個行業乃致一整個城市。有甚麼想跟年輕的創作人說嗎?黃修平想也沒想過就回答,似乎已將同一答案告訴自己學生很多次:「1. 鍾意做創作嘅繼續創作,不斷創作。2. 參加比賽,ifva又好,影意志又好,我最近參加大阪電影節泉州電影節,佢地嘅短片比賽質素都好高,我地香港人應該參加多啲。3. 搵一啲可以探討嘅題材深刻地探討。大家可能都覺得有啲犯禁嘅題材值得嘗試,我自己唔係咁睇,反而喺一啲唔犯禁嘅話題講好一個故事,咁樣係更加重要。」
整段對話,黃修平隻字不提數字,甚麼成本,票房,投資都一概不聞,只問創作技巧,深度,體會,觀察。筆者忽爾想起黃修平很多年前說過自己不想拍大製作,想做些更貼近人的故事。突然,黃修平正經地望著我,近乎太過嚴肅地說:「有啲價值係唔會消失。我地要努力做好本份,迎接好日子嘅來臨。」
我隱約看見幾泛淚光,大概是看錯了。
|《分號》英國團隊
撰文 // @iamkandogxd
攝影// @_jtse_
分號 INTERLUDE HK 2025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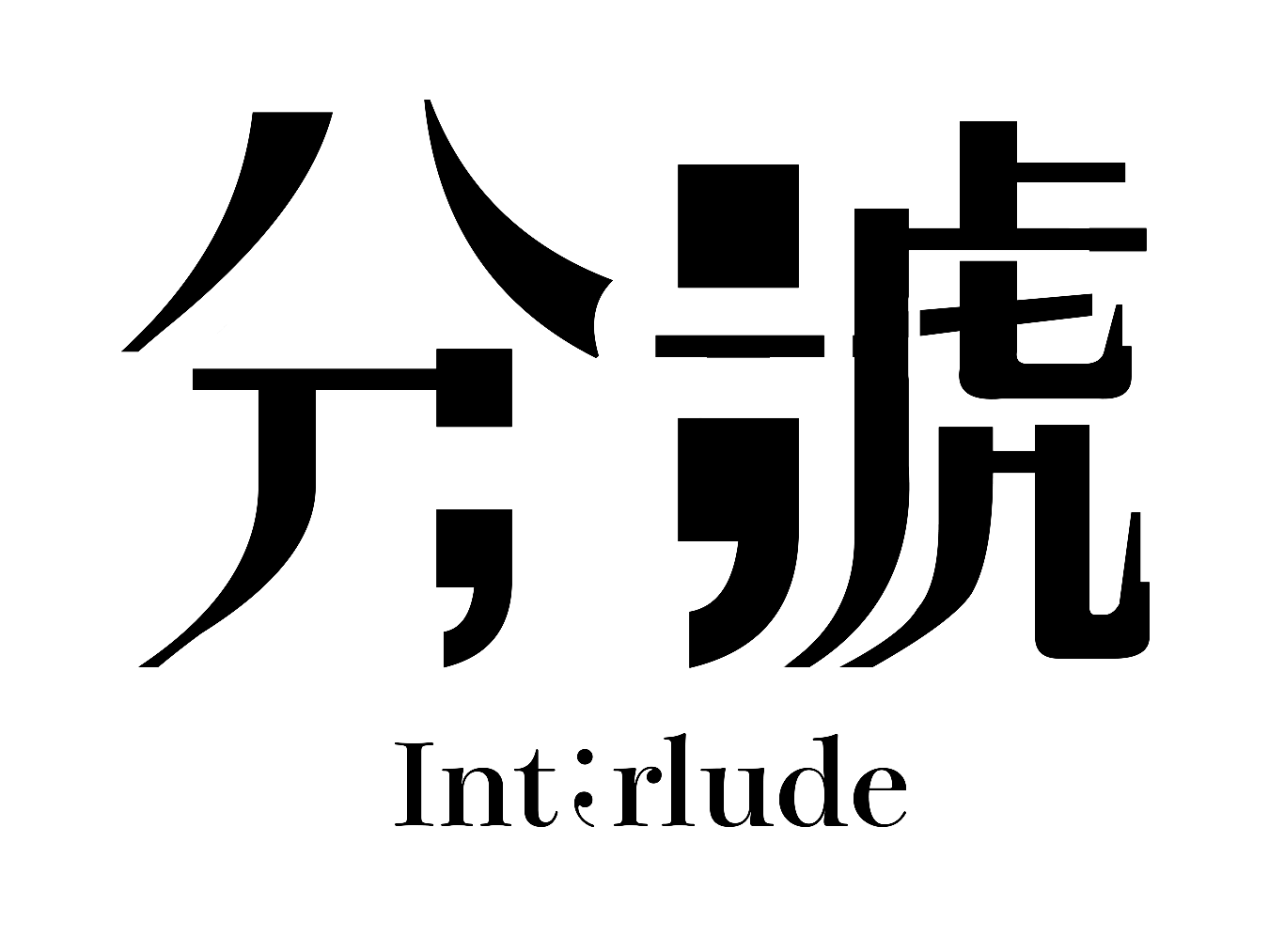


發佈留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