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月的最後一日,百老匯電影中心內的人龍盤纏到外,繞成半圈。夏日的香港,當日天文台錄得全月最高的34.7度,熱氣蒸騰,影迷們在暴烈陽光下幾近睜不開眼。探頭一看,原來是中國電影《漂亮朋友》的主演來到香港與觀眾見面。黑色桌後的耿軍導演、新晉金馬影帝張志勇、演員薛寶鶴以及配樂陳筱舒正不斷在海報、衣服甚或帽子上簽名,望能讓影迷們滿載而歸。
《漂亮朋友》上映後,港台兩地反應非常激烈。臺灣金馬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譽其為「華語同志電影天花板」;第四十九屆香港國際電影節,《漂亮朋友》一票難求,不少來自中國的影迷特意南下,一睹電影風采;而在香港文化中心進行香港首映時,觀眾們更是捧腹大笑(相信我,真的是這樣),笑聲不絕於耳。可謂雅俗共賞。
這部電影是如何誕生的?
三位熱愛電影的鶴崗青年
或許,一切都要從冰天雪地的鶴崗說起。
戲裡戲外,鶴崗一直都是一個對耿軍而言極為重要的地方:在其作品《錘子鐮刀都休息》(2013)、《輕鬆+愉快》(2016)、《東北虎》(2021)中,都不難找到鶴崗的影子。在戲外,耿軍從小便在鶴崗生活,少年時家中物資匱乏,父母又忙身於外,沒有時間理會他和弟弟,不受束縛的他們得以跑遍鶴崗的每個角落。因此,對其而言,鶴崗就是一個溫暖的、充滿回憶的地方。自己寫劇本時,不免自然而然的想到這個承載了自己半生的城市。後來,鶴崗這個地方更在無形之中把耿軍、張志勇、薛寶鶴這三個有著電影夢想的人連結起來。

耿軍最初開始拍片時,不過手拿一部DV機,演員則大多是身邊的朋友——他對演員的標準只有一個:只要唱K不走音便可以。不成規模的劇組、簡單的器材、業餘的演員,背後卻藏著極大自由,足以讓他不斷的摸索自己的創作邊界。
在耿軍第二部影片《散裝日記》(2003)中,張志勇就加入了。二人相識於微,耿軍想,既然張志勇唱歌不走音,又是自己的朋友,那麼不如一起拍片吧?這一個念頭,幾近把二人的生命軌跡完全扭轉,讓他們在創作路上走了超過二十年,至今未停。

薛寶鶴的加入則曲折離奇得多。本來他在鶴崗電視台有一份穩定的工作,但他知道自己想要的不是這些:小時候看完西遊記,他總愛幻想自己是騎著筋斗雲的孫悟空,或是手拿三股鋼叉的黃風怪——他朦朧的知道,與影視相關的一切,自己都極有興趣,也因此才選擇與影像相關的工作。然而,偶然的碰面又讓薛寶鶴的人生拐了個彎。2009年的一日,耿軍和張志勇為準備《青年》(2009)的前期工作而到鶴崗電視台租借器材,一見他們,薛寶鶴便極有興趣,開始整天纏著他們,希望能夠參與其中——他逐漸清晰的意識到,這就是自己所嚮往的生活。2013年,耿軍向其拋出橄欖枝:「你敢不敢演個女的?」,薛寶鶴想也不想便答:「這有什麼不敢的?」但其實他連劇本說些什麼都不知道。結果,他便在《錘子鐮刀都休息》(2013)中初次亮相,飾演一名以詐騙維生的婦人,這是後話。

對創作而言,朋友的身分或許是一道雙面刃。因為是朋友,所以能夠暢所欲言;又因為是朋友,所以溝通時或許有所避忌,害怕不小心便傷了彼此的心。張志勇和薛寶鶴都覺得,這一身份有助他們創作。從構思劇本起,耿軍便會讓他們參與其中,彼此對劇本的理解會更深入;演員之間的相處也會更為融洽。拍攝期間,每日晚上,會議室桌上都會放著各式各樣的食物,大家會一邊大啖著各種美食,一邊探討劇情、排練。薛寶鶴甚至覺得,「這更像是一個家庭」。
從《錘子鐮刀都休息》(2013)開始,角色的名字都來自演員的本名。例如張志勇飾演的角色名就叫張志勇(《東北虎》除外);薛寶鶴飾演的角色名就叫薛寶鶴。這種設計背後其實反應了耿軍對電影的想像,他覺得,現實中我們各自過著各自的人生,而電影裡面的角色則能讓我們感受不同的命運、情感。電影作為集體創作的產物,變相角色的靈魂是由創作者所賦予的,因此,「電影裡面的每個人物也是我們自己的人生,其實是電影有機會讓人生更豐富,像楊德昌導演所說的『電影能延長人三倍生命』。」
漂亮朋友們的掙扎

或許,作為異性戀,要飾演同性戀者便已經是一大障礙,畢竟未必能夠完全明白對方的想法;而在中國飾演同性戀者,更是難上加難。張志勇坦言,一開始聽到耿軍說要拍同志題材的電影時,內心的確有所掙扎,他自己也不太了解同志群體。後來,他們有機會接觸同志們,在相處的過程中開始逐漸了解他們,加上各種電影、資料,終於成功突破心理障礙。薛寶鶴則直言,即使有不同的鋪墊、幻想過有可能會出現什麼類型的表演,但收到劇本的一刻,還不免咋舌:「哇,這個是什麼樣的?」,也因此,後續功夫非常繁瑣,他們要不斷的去探討、去思考這個角色的動機,去想怎樣才能讓觀眾覺得角色的行為是正常的。「特別是我吧,我這個角色我希望他能不被人討厭。」在電影中,薛寶鶴所飾演的角色求愛不遂,幾近犯下強姦。
掀起不少話題的,還有電影中一對女同志所哼的幾近外星語的洗腦旋律。這有賴於耿軍對配樂陳筱舒的無窮信任,還有她自己的無限創意。一開始創作時,陳筱舒直言特別緊張,不斷懷疑自己到底能否完成作品,多得耿軍鼓勵,後來自己不斷摸索,終於漸入佳境,「越寫越嗨,越寫越放鬆,然後自己就越寫越快樂。」成功創造出自己滿意的作品。
混雜的香港記憶

在香港文化中心首映時,觀眾們掌聲雷動。薛寶鶴站在台上,激動的說「首先,我是一個看香港電影長大的孩子,然後,我今天以演員的身分來,像做夢一樣」。
中國改革開放後,開始引入香港影視。1979年,麗的電視和無綫電視分別在廣州舉辦新春賀歲活動。到1980年代,各省市電視台進一步開放,紛紛引進香港電視劇《射鵰英雄傳》、《上海灘》、《流氓大亨》等。一時間,大量港產電影、電視劇湧入中國,為一時文化現象。在70年代中,80年代初出生的耿軍、張志勇、薛寶鶴三人,少不免受到香港電影的影響。
一提起香港電影,薛寶鶴便雙目發光,如數家珍般説出那些演員、導演:周星馳、成龍、李連杰。有時候,他會看完再看,看完再看。對張志勇而言,香港電影更是舊日的鶴崗剪影,混和了年少時代的觀影體驗。他說,以前在鶴崗的錄像廳,只需要兩塊錢,就能夠看到一齣香港電影。耿軍的觀影光譜則最為廣闊:從吳宇森到三級片,從三級片到許鞍華、王家衛、譚家明均有涉獵。銀幕上傳來的連環槍聲,飛車場口構成了他對香港最初的印象:「我們在童年時期看電影的時候,我們覺得香港街頭會開槍,街頭會撞車」。電影學者大衛博維爾(David Bordwell)曾如此評價香港電影:「盡皆過火,盡是癲狂」,或許也呼應三人對香港電影的印記。但當真正來到香港,看到百老匯電影中心旁的舊油麻地警署簇擁著眾多遊客時,他們便醒悟了——香港其實是一個以旅遊為主的安全城市。
電影與城市景觀是密不可分的。薛寶鶴第一次到香港,第一件事便是到重慶大廈打卡——因為在《重慶森林》(1994)中,何志武曾經奮力奔跑,跑過人滿為患的重慶大廈;其後,便從中環乘扶手電梯到半山,因為阿菲曾經躲在窗後,偷窺正在搭扶手電梯上班的663;再後來,就到油麻地、尖沙咀、銅鑼灣等地逛一逛,因為「這些地名,它就存在於我們的青春回憶中。對我們來說,香港的這些文化符號特別的重要。」
一如楊德昌在《一一》所說,「電影發明以後,人類的生命比起以前至少延長了三倍。」對他們三人而言,電影所帶給他們的或許更多:從東北小鎮鶴崗到臺灣金馬影展,從金馬影展再到電影中心,加上大大小小的電影節,早就不止三倍了。訪問尾聲,薛寶鶴說,「我覺得這樣的人生非常的魔幻,讓我的人生增加了很多維度,所以我現在坐在這,還是會覺得有一種奇妙的幸福感。」電影萬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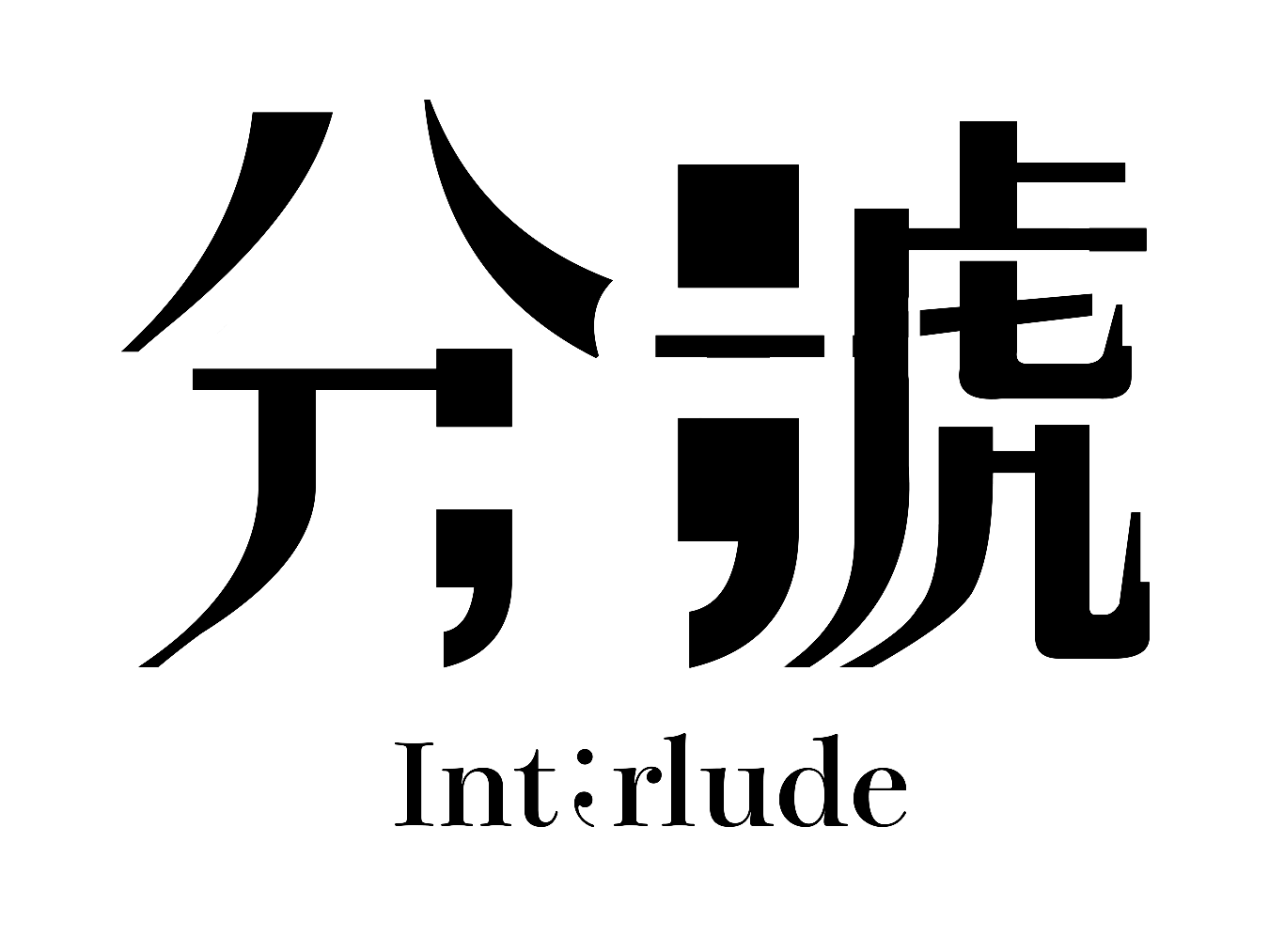


發佈留言